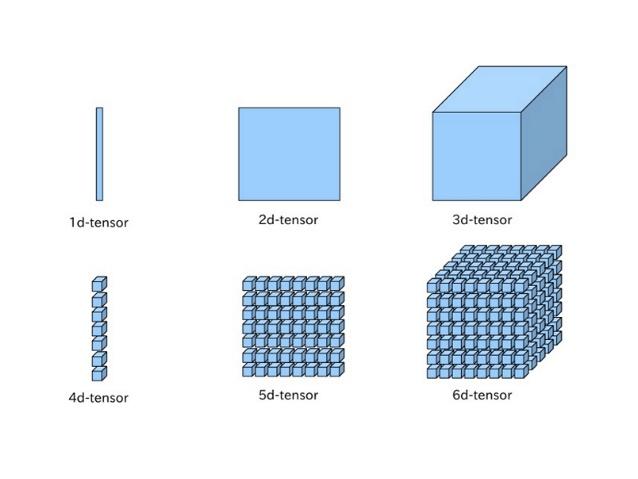The Analysis of Time
对时间的分析
时间——和空间一样,我们难以为之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。所以如果选择直接面对它,只会让人束手无策。而手表,蕴含着我们和它的相互作用。所以我们的分析就从手表开始。
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这里的手表并不局限于“腕表”或者“智能运动手环”,只要我们通过某种仪器设备得知时间,它就在“手表”的讨论范围之内。
手表,从它的名字开始,就蕴含着它和人的关系:是人们戴在手上的设备。而“表”则昭示着它的基本使用价值:让人们方便地得知这一刻的时间——一种和地球周期运行有关的信息。
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时间,而且要求一定的精度(比如到秒)?虽然“时间”这一概念对科学研究而言非常重要,但一个稍微对地球运转有经验的人,都知道日出大概应该起床,日中大概应该吃饭,日落大概应该下班。为了调节自己的工作和休息,似乎只需要知道现在是一天中的几分之几即可,精度是不必要的。
然而我们的学习生活处处都需要一个较为准确的时间,但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我们强调“时间观念”,赞赏“守时”的人,批评“迟到”的学生。人类用循环往复的运动创造出“时间”的概念,把一个大的周期不断用小的周期分割,去掉模糊性,从而能够说“现在是18:20”。而接收到这一信息之后的学生们,第一反应就是“该下课了”;如果听到“这是 ddl”,那么我就必须在这一时间之前完成指定的任务。我们使用精确时间来设置节点,这个节点前和后存在一些差别,但是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间,这种差别才能成为现实。
人与时间的关系,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:一个约定。我们用一个精确的时间来为自己立法,让“守时”成为道德评价标准。我们约定现在下课,要是老师还滔滔不绝,学生会抱怨“拖堂”;我们约定这是 deadline,那么过了这个 line 你就 dead。可见,时间充当了人们相互联系的协调者,通过给我们下一步行动以依据的方式,让社会运转更加有序。
但时间并不满足于充当“协调者”的角色。现在,它愈发凌驾在万人之上。而当人们带上手表的时候,也成为了时间的奴隶:手表作为它的使者,将标准传达给所有人,调和组织人们的行为,从而将时间本身的有序性转化为人类社会的有序性。在这个过程中,时间从一个人造物的躯壳里挣脱出来,挥舞大棒,号令一切。
那根大棒,正是有着强制和命令色彩的 deadline,或者更广义地,由精确时间自然衍生出的时间节点。很多人认为现在生活节奏变快了。所谓“节奏”,是时间节点的密度和强度;而节点前后受到的奖赏或惩罚,逼迫我们不得不为眼前考虑——考虑那些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事物,而不是我们自己。可以说,精确的时间带来福音的同时,也否定了个体的独立。
从上一个节点到下一个节点,人们做了很多。然而对“时间变快”的指认,很少在做的过程中进行——抱怨总是发生在最后。这可以解释为由疲于奔命而忘却了时间的流逝。于是,当我们说“怎么一年又过去了?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呢!”时,我们认为自己本该做哪些事?
为了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,我们先看看“快”的对立面:“慢”。面对这日益“加速”的生活节奏,“慢下来”成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口号。他们口中的慢,通常是这样的:“停下手中的事情,发一发呆,在一个惬意的午后拿起一本感兴趣的书,洗一洗积累了一周的衣服。”另外,我们总是将童年比作“金色时光”,那时的时间似乎也是“慢”的。
我们为什么需要慢?我们在说“慢”的时候,究竟在说些什么?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多大价值,却能“放慢时间”的事情里,究竟蕴含着什么价值?
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当我们逐渐被日益紧张的ddl限制、本应属于独立自主的时间日益被别人安排,做完任务后感到的疲惫和空虚让我们意识到,生活原来不是自己的,而是他人的。所以忘却 ddl 时,那个用于人际协调的精确时间也连带地被忘却了,退回到一个较为模糊时间上来——一个更多用于协调自身的时间概念。而这一退化,表面看来是“享受生活的美好”,实际上是向愈发紧迫的时间节点发起的反抗。
此时,上位者们正利用时间节点的道德性和强制性来掩盖他们的实际目的。资本家们精巧地设置 ddl,让打工人们不得不拼命干活或者延长工作来完成他们的任务,以期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。而美团外卖推出的“愿意再等五分钟”按钮,更是将本由 deadline 联系的平台-快递员剥削关系偷换为消费者-快递员强迫关系,再为之粉饰“愿意”的道德面纱,可谓居心叵测。
紧张的送餐 ddl 已经让快递员们逐渐无视交通规则。为了免于惩罚,将和剥削者的约定放在了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约定之上——资本家们看到这一幕时,应当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而那些每天活在无尽 ddl 中的快递员们(今天做完,明天还有!),想必是当代,认为时间过得最快的一群人。